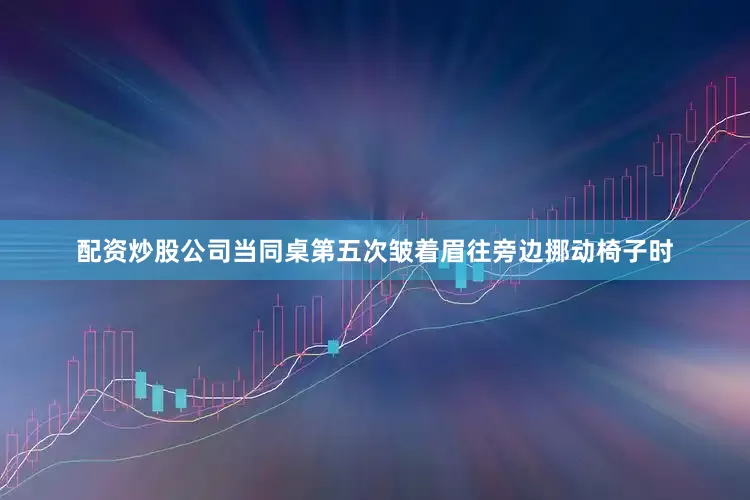
九月的阳光透过教室玻璃窗斜斜洒落,粉笔灰在光束里轻盈起舞。当同桌第五次皱着眉往旁边挪动椅子时,我才惊觉自己又在无意识地吸鼻子。从两周前那个普通的晨跑后开始,鼻腔里仿佛住进了淘气的小精灵,时不时用毛茸茸的尾巴撩拨神经,引得喷嚏一个接一个,纸巾在课桌里堆成了小山。
起初校医开的滴鼻液还能勉强维持表面平静。数学课上,趁着老师转身板书的瞬间,我迅速仰头滴药,冰凉的液体滑入鼻腔的瞬间,呼吸像被突然打通的隧道般顺畅。可药效消退得越来越快,到后来即便课间连滴三次,下节课依然会被汹涌的鼻涕和胀痛的鼻窦折磨得无法集中注意力。生物课上讲解过敏反应的章节时,我盯着课本上过敏性鼻炎的配图,手指不自觉摩挲着自己发红的鼻头,眼眶突然发烫 —— 原来这密密麻麻的文字,说的就是我每天的生活。
父母带着我穿梭在城市各大医院的耳鼻喉科。西医诊室里,戴着金丝眼镜的医生将细长的探头伸进鼻腔时,我紧张得攥紧了检查床的床单。“典型的季节性过敏性鼻炎。” 诊断结果伴随着一摞药盒:白色小药片是抗组胺剂,喷鼻剂需要精准对准每个鼻孔按压。中医馆弥漫着浓重的草药香,老中医把脉后写下的药方里,苍耳子、辛夷花等字眼看得我头晕目眩。每天清晨六点,厨房里都会准时响起砂锅咕嘟冒泡的声音,褐色的药汤苦涩得让人舌根发麻,却不得不捏着鼻子灌下去。
展开剩余54%这些努力换来的只是短暂的平静。月考时,持续的鼻塞让我脑袋像裹着层棉花,原本擅长的英语听力题变得模糊不清。当我第三次擤鼻涕震得整张桌子发响,前排同学终于忍不住回头,那道带着嫌弃的目光像根刺扎进心里。回家路上,我对着街边橱窗里的倒影,看着自己因为频繁擦拭而脱皮的鼻尖,泪水夺眶而出。
转机出现在社区医院偶遇的张阿姨。她拉着我展示手机里孙子的鼻炎康复照片,兴奋地推荐她儿子从国外带回的口服和鼻炎喷。“这内服的能调理体质,外抹的直接作用在患处,双管齐下!” 抱着最后的希望,我开始了新的治疗。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清新世界的窗。
第一周过去,变化微乎其微,我几乎要放弃。直到某天早读课,当晨读声整齐响起时,我突然意识到 —— 自己竟然能用鼻子顺畅呼吸了!鼻腔里不再有那种肿胀的压迫感,空气带着书本的墨香和清晨的露水气息,缓缓流入肺部。从那天起,症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轻。三个月后的期中考试,我终于能全神贯注地答题,当笔尖在试卷上流畅滑动时,窗外的蝉鸣声都变得悦耳动听。
如今的我,书包侧袋里依然常备着鼻炎膏,但使用频率越来越低。每当看到校园里那些被鼻炎困扰的学弟学妹,我都会主动分享自己的经历。这场与鼻炎的战役,不仅让我重获健康的呼吸,更教会我:在困境中坚持寻找希望,终会等到破茧成蝶的那一刻。
发布于:北京市按月配资开户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
- 上一篇:中国前十股票排名那可是图片界的魔术师哦!海量美图模板加上炫酷滤镜
- 下一篇:没有了



